是谁成就了巴罗洛?
2015-03-03 14:32 来源 : 酒斛网 作者 : 孙姑娘
分享
“Barolo Boys”这部纪录片,我已经看过不下5遍。一个处女座看过一系列Discovery和BBC后会对那些逻辑、场景或配乐不够精致的片子嗤之以鼻。Barolo Boys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无法与前两者相提并论,但从葡萄酒纪录片匮乏的角度看,它让人们关注到一个时期和一群人,接着就剧终了(这种只提出不解决问题的做法我们要强烈谴责)。
如要看懂这部纪录片,手边一定要有Kerin O'keefe那本“Barolo and Barbaresco: The King and Queen of Italian wine”。这时,文字比话语更有逻辑的特性很好地凸显出来。第四章详细地解释了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将这段时期这场革新的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顺带用Barbaresco的发展进行类比。纯粹看片,容易对这批革新者产生更多负面的看法。作为一个保守派,老一辈人的做法一定是有道理的,一味的摒弃并不是最佳的选择。看书之后,这次革新的意义所在就非常明显,更能身临其境地感受他们在那个年代的不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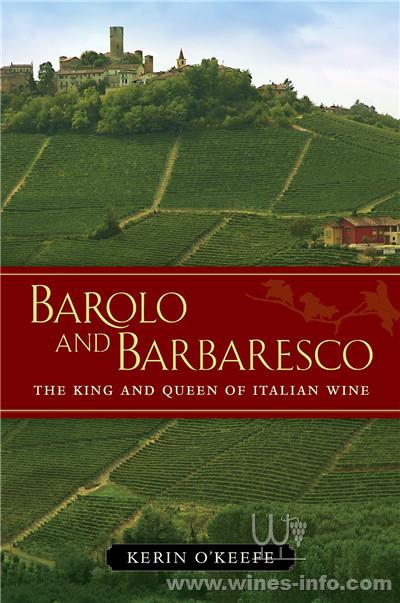
Barolo and Barbaresco: The King and Queen of Italian Wine
二战之后的意大利可谓“千疮百孔”。196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以及左翼组织的恐怖活动让经济,也包括葡萄园的经济停留在“生存”阶段(此段来自维基百科)。对于大部分Alba的农民而言,葡萄只是经济作物的一种,而且不是最赚钱的。Sylvia Altare(Elio Altare之女)在片中回忆说她的祖父在地窖中同时放置着四个斯拉夫大木桶、牛、鸡和一个加热器。葡萄,或者说葡萄酒无法让他们获得温饱,他们需要种小麦、果树、榛子、养鸡和放牛。新一代还认为之前葡萄浸皮时间较长是因为老一辈无法全心全意酿酒,这事我们之后再说。
纪录片开场提到,“1969年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拖拉机,人人都在用牛耕地”,“许多人都直接出售葡萄,不能酿酒”,却忽略了那个让发展停滞的核心问题——水资源匮乏。你心想,几乎每个著名产区都依水而存,说人家缺水不是开玩笑吗?可是你知道吗,直到1980年代中期,Langhe偏远的村庄才有持续供水。你也许记得皮埃蒙特有条著名的Tanaro河,它流经巴罗洛产区。但你不知道沿河打水非常昂贵。为了生存,人们一直使用井水,而到仲夏早秋时节,由于地下水位下降井里无水可用,用水难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Tanaro 河
也就是因为用水困难,酒窖的卫生问题才会显得格外严重。用酒农Mauro Veglio的话来说:“在酒窖中用水是闻所未闻,更是亵渎圣洁的一件事。”缺水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阻碍果农向酒农过渡。果农无法自酿,就只能持续不断地将果实卖给酒商。那是个买方市场,果农没有任何的议价能力。Elio Altare说:“1975年的葡萄长势非常好,成熟、漂亮。我却只能跟其他果农一起站在Alba的广场上希冀有中间商把我们的葡萄买走。而直到葡萄开始过熟,要烂不烂时,中间商才以极低的价格买进,还说来年春天再付钱给我们。”果农的失望不言而喻。
正所谓“有压迫才会有反抗”,这话同样适用于经济发展。这样一批二十出头、年轻有冲劲的果农们想要改变现状,就像他们的先锋邻居Anjelo Gaja一样,酿出有质量的酒。他们开始接触外面的世界,屡次前往勃艮第(不只有片中提到的那一次),迫切地想知道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同仁们是如何做到只种葡萄又酿好酒还能靠这个活得很好。就这样,先进的葡萄园和酒窖管理技术被带回到山这一边。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法国,美国纳帕谷也在这场革新运动中起到影响。
“Botti,这种斯拉夫尼亚橡木制成的大桶,成为两代人冲突的一个焦点。”Kerin在书上写得很清楚。而这个桶更是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使Altare两父子矛盾最大化。父亲Giovanni固执地使用大型木桶:“前人都是这么做的,难道你的方法会更好吗?”。而儿子Elio更关心那些桶正在被虫蛀、被腐蚀、开始漏液。墨守成规和年轻气盛放在一起就像火上浇油。父亲往果树上喷农药把儿子送进医院,儿子回来就把果树和木桶都砍成柴烧。结果,父亲剥夺儿子的继承权,儿子把父亲从酒庄上除名。两败俱伤,不是吗?
现在看来,Elio Altare不过是一位努力接受新鲜事物,把“崇洋媚外”做到极致的年轻人罢了。当他看到受称赞的同行们使用的都是法国小桶也跃跃欲试,这本身并无可厚非。来自米兰的银行家Giampiero Cereda更是第一个将法国橡木桶带到Langhe地区,助其一臂之力。他们瞒着其他人,从50升的Fusto桶,114升的Feuillette桶,150升的Cigarillo桶,225升的Barrique桶,到350升和450升的Tonneau桶,一一实验过来,1983年Elio才决定使用Barrique桶。你可以说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检验他们选择的正确与否,但你不能简单粗暴地说人家是“拍脑袋”做出的决定。

不同尺寸的桶
法国桶是酒窖技术的改变,那绿色采收就是葡萄园种植的革新了。这一技术被认为“将同等的能量输送给更少的葡萄,以提升最终的品质。”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的事情,当年保守的村民可是请了牧师过来压惊的。Barbaresco的Gaja再一次成为先驱。Elio Altare紧随其后从其父手中夺过剪刀。Chiara Boschis则跟在雇的农民身后再剪一遍。Michele Chiarlo没那么幸运,他无法说服忠实的农民,只能曲线救国,租用葡萄园以进行绿色采收。时至今日,还是有人不认同这个做法。Maggiore,89岁高龄的葡萄园工作者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放弃这些成熟漂亮的果实。“以前我们把它们都留着,用来酿很多很多餐酒。”他说。
如果说这之前都是“单打独斗”,那1986年的“甲醇丑闻”让他们真正凝聚在一起,召唤出更强大的“巴罗洛男孩”。23人死亡,数人失明都源于酒商添加甲醇来提高酒精度,导致国内外消费者闻“皮埃蒙特”色变,市场销售停滞,日子越发不好过。于是,这群年轻人开始定期聚会,互相盲品去感受更好的酒,坦诚地分享自己的实验方法。虽说是老生常谈,但正是这种“小组讨论”的模式让他们获益匪浅。就像Giorgio Rivetti所说:“一位闭门造酒的酒农,一生也只有40到50个年份的经验。而10位有共同目标的酒农一起酿酒,他们将迅速成长。”
酿出好酒,也得有人识货。一位美意混血酒商Marco de Grazia就这么进入他们的圈子,把巴罗洛这个名字带到美国。适逢美国人民受够Chianti Classico与Spaghetti搭配,经济复苏让他们开始寻求更奢华地道的意大利美食美酒。不要忘记了,1988,1989和1990都是巴罗洛难得的好年份。尤其是1990年那温暖的生长期,给Barolo和Barbaresco带来更柔和圆润的单宁,再配上新橡木桶的香草、巧克力和木头味,一下子就抓住了消费者饥渴的味蕾。市场供不应求,价格水涨船高,欣欣向荣的景象让越来越多的酒农在90年代早期开始酿这样的酒。巴罗洛在一个快餐风靡的国度火了。
那时,不论是美国、英国的酒评家还是意大利的葡萄酒指南都对浓郁、过度萃取、过度橡木的Barolo和Barbaresco趋之若鹜。他们好像怎么都喝不够一样,一个接一个的给这些内比奥罗特征不甚明显的酒打出高分,意大利三杯奖也接踵而至。Alessandro Ceretto明确指出:“90年代获得三杯奖的酒,价格马上就翻番。然后你能再种上一公顷的葡萄园,买入更多设备。现金流的涌入使酒庄经济大幅度好转。”Chiara Boschis则更感性:“我们拿三杯奖就像演员拿奥斯卡一样。”这一位可是公认的第一个100%使用新橡木桶的酿酒师。

不论你喜欢与否,都不能否认这群年轻人创造出一种受众人喜爱的口味,就像可口可乐的发明一样。说得俗气一点,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贫困许久的年轻人怎会不想多赚一点,过上更好的日子,这不是人之常情吗。Lorenzo Accomasso,一位传统的酿酒老人也承认:“如果我有10个法国木桶,我也能很快征服世界。”Eilo Altare在与Bartolo Mascarello的公开对话中说道:“诗歌固然美好,填报肚子更重要。”在向Elio Altare询问其本意之前,我们不好妄自揣测他的想法,但“盛极必衰”是我们所能预见的。
那场世纪对话中,Bartolo Mascarello说:“我们很欣慰Elio这样的年轻人坚守在葡萄园中,我们所遗憾的是他们跑到法国去学习如何酿我们意大利的酒。”随后,媒体如“墙头草”一样开始批评这批新新人类的酿酒方法,说他们如何抹灭了巴罗洛的特性,而向现实妥协。并称“他们的革新源于巴罗洛的传统,而他们还不自知。”事情发展到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用桶或绿色采收的问题。大家关注的焦点已经变成“是谁推动了巴罗洛的发展?”新派认为自己才是那个关键人物,老派就说做人不要太自负,应该用历史的视角来看问题。
消费者的口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开始厌倦太过丰满,化妆过浓的酒,转而寻求更真实的味道。片中老牌的英国进口商David说,“内比奥罗就应该优雅的陈年,充满水果香气。而不是我在九十年代初期尝的好莱坞大片,完全不知道主角是内比奥罗。”你也不要认为葡萄园工作者不懂酒,为Chiara Boschis做事的Maggiore说:“如果以前人们在酒中尝到木桶的味道,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酒送去蒸馏。”Marta Rinaldi也说,Bartolo Mascarello看到今天的发展应该很欣慰,经过长时间浸渍、大木桶和长时间陈酿的酒现在终于能一雪前耻了。(这话也只有喝过40年代老酒的富三代才说得出来啊!)
如果说纪录片是百(que)花(shao)争(zhu)鸣(jue),Kerin的书就更像一(you)家(suo)之(pian)言(hao)。她坦言,比起大浓妆,更喜欢裸妆,而Elio Altare就是被表扬的代表之一。作为在巴罗洛地区用法国桶的先驱之一,他坚持到今天,并成功进化成“玩桶而不被桶玩弄”的代表,这与那些用桶去掩盖葡萄先天不足的酒庄是截然不同的。尽管他的巴罗洛在法国桶中陈放24个月,你仍然能感受到内比奥罗天性里的覆盆子、红醋栗、野玫瑰等芳香,而不是傻乎乎的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
我们似乎看到这个“团队”的解体。Roberto Voerzio,“巴罗洛男孩”之一说:“1997年我们只用法国桶。1998年我们开始购入1200升、1500升、2000升和2500升的大桶。”之后Vietti家、Chiara Boschis都开始买大桶。意大利人各自为政,开始走自己的路。用Giorgio Vietti的话说,对“100分”的追求和对“金钱”的渴望让嫉妒窜了出来。一些经历过新派的酿酒师开始接受老派的做法,创造出处在中间风格的酒。要么,他们进行十来天的酒精发酵,做两个星期的浸皮,然后在新旧桶中放上一年,在斯拉夫尼亚大桶中再放一年。要么,他们采用法国旧桶,或500升的tonneaux桶。最终的成品,能在年轻时饮用,也能适度陈年。带有一丝香草熏烤的气息,又保留了黑樱桃、皮革和玫瑰香。
故事到这里也该告一段落了。我喜欢Marta Rinaldi在片中说的:“现在就给巴罗洛的历史是谁创造的下个定论还为时过早。”谁知道再过去几十年,人们的口味会变怎样,是继续追寻“本质”,还是让浓重的木桶重新站上舞台,你知道吗?反正我是不知道。
Elio Altare

法国桶坚定的捍卫者,激进的改革家,也是巴罗洛地区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酒庄现在很多工作交给其女Silvia Altare打理,自己开始在Cinque Terre地区种葡萄酿酒。
Mauro Veglio

一直跟Elio Altare做邻居,在酿酒方面深受其影响。不论是从果农到酒农的转型,还是耕种酿造技术的革新。更重要的是,现在开始降低新木桶的使用,只使用轻微烘烤的木桶进行陈年。
Angelo Gaja

Gaja酒庄是Barbaresco法定产区最古老的酒庄,Angelo的父亲也一直致力于提升质量。Angelo本人毫无疑问是意大利最成功的酿酒师之一,也是他对两个产区的质量进步起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Chiara Boschis

被认为是巴罗洛第一位女性酿酒师,她热情且自信。其家族从Pira家族手上买来酒庄,之后Chiara就大刀阔斧地进行她认为正确的耕作及酿酒理念。今天,她还是坚持使用法国新木桶给巴罗洛进行陈年。
Michele Chiarlo

以Barbera d'Asti闻名的酒庄,在巴罗洛和Barbaresco都有酿酒。少有的父子一条心,让他们排除万难进行绿色采收。其子Stefano是专业的酿酒师和农业师负责酒庄酿酒。
Giorgio Rivet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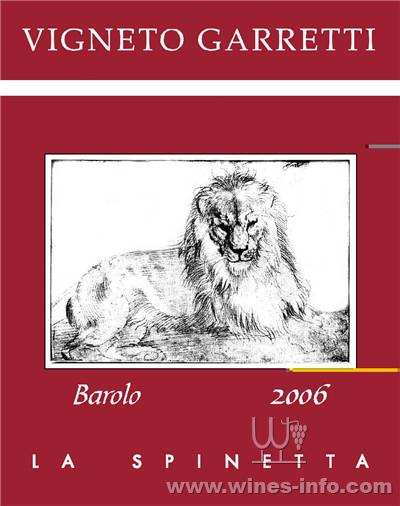
他是La Spinetta酒庄的主酿酒师,也是法国橡木桶和现代技术的粉丝。每次绿色采收,他都会去现场监督。酒庄同时在巴罗洛和Barbaresco酿酒。他的巴罗洛坚持在法国新木桶中陈上一段时间。
Alessandro Ceretto

Alessandro曾经也是法国新木桶的拥趸,追求浓郁和橡木味。现在,他的味蕾也开始改变,更希望自己的酒展示出自然赋予的一切。2008年起他减少新木桶和小木桶的使用,酿酒哲学已然变化。
Lorenzo Accomasso

这位开放且坚定的老人也是Elio的邻居。他与姐姐一起照顾三公顷的葡萄园,酿酒和销售。从70年代开始,他就在冬天大量剪枝,以获得更高质量的葡萄,并采用低温发酵。因产量很少,你偶尔可在德国和日本买到。
Bartolo Mascarello

经典大桶派巴罗洛的捍卫者,一位睿智的老人,2005年去世。酒庄现在由其女Maria Teresa Mascarello继续经营。只酿一款巴罗洛,由四块不同葡萄园的葡萄混合而成。
Marta Rinaldi

著名酒农Giuseppe Rinaldi的女儿,2010年加入酒庄,与父亲一起工作。酒庄之前酿造两款由两块不同葡萄园混合的巴罗洛,但2010年欧盟的法律不允许双葡萄园出现在酒标上,因此酒庄修改了混合比例。
Roberto Voerzio

中庸的法国桶使用者。97年时还全部使用法国橡木桶,之后就开始买入大型木桶。现在他的巴罗洛在旧法国桶和大桶中混合陈年。